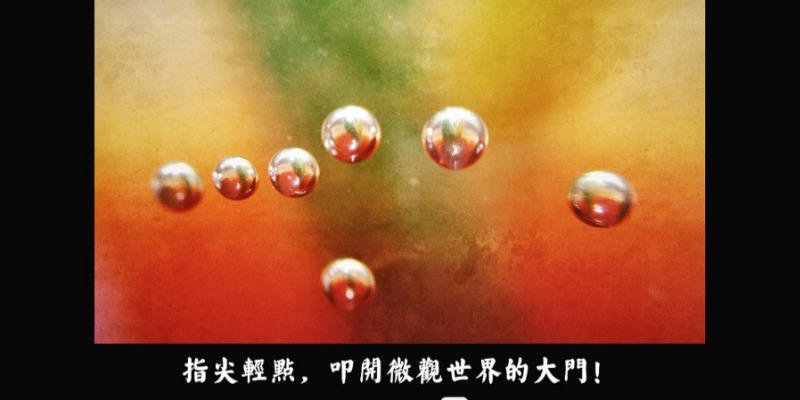编者按:昨天宁老湿和多年兄弟笑天来到一个拉面馆。虽然时常联系,但是我俩真的好久没见了。笑天是我原来在报社的兄弟,比我大两岁,他转到摄影部的时候我接了他编辑的工作。原本以为我有天可能也会追着他也能专门做摄影记者,没想到07年一场事儿,他去了另一家报社,我离开了新闻单位。此后我在家赋闲4年,反而和他接触很多。他给我介绍些拍摄的工作,我们一起扫街。
笑天是少有的让我很服气的摄影师。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:不服就斗片子。这是需要非常深的摄影功底才敢说的。后来在我认识的人里面敢说这话的无非两个人,一个是周日一起讲课的姜磊老师,一个是国家地理的王宁老师。当然,我自己也敢说。
这组片子我知道他是很多年前拍的。至于内容,大家还是自己看吧。我只想说,我希望这个选题能够成为一本画册。
正文:
这组照片从2010年6-7月拍摄完成,报社和几家杂志使用后就一直深藏在电脑硬盘里,并不是忘记或不在乎,只是每次再看都会再次翻涌很多思绪!去拍背夫并不是突发奇想,记得在十几岁的时候去爬银川西边的贺兰山时就遇到过背夫,当时他们突然出现在山里又突然消失,来不及看清面孔只有背影留在我的记忆力——那些巨大的石块几乎遮挡了上半身的躯干,他们从哪来,到哪去?十几年后,仅凭当时的短暂回忆我又回到贺兰山,寻找他们。
那是一条没有路的“路”,只有越野车和皮卡能开到这个只有两排砖土平房的住地。我的突然到来,让他们显得有些拘束,这可能是他们在山里时间久了,与外界的接触变少的缘故。天空大亮前吃过那简单不能再简单的早饭一个馒头一碗白粥,就和他们出发上山了,而我在第一天出发前把所有的相机镜头都留在了住地。

简单的早饭,他们边吃边聊着。

鄢军,这个基本不说话只是微笑的健硕男人在和我熟悉后聊了很多。

每次递给鄢军的烟,他都舍不得马上抽掉,夹在耳边只是笑。
一路上,其实根本没路,我没说话也没人和我搭话,只有鞋底与石块的摩擦和偶尔的吆喝声在山谷里回荡。半小时后大家都聚集在一块巨石下,几个人像变魔术一般的拿出了很多水桶。我问这是从哪冒出来的,苟宗德说是藏在大石头后面,其实根本不用藏,这根本没人!说完,笑的满脸又深又瘦的皱纹堆在脸上。在大石侧面有一处泉水出口,大家陆续接满了水桶。我问这是路上喝的水吗?鄢军告诉我,这是给山上看矿人背的水,他不能下山,吃的喝的都要我们给背上去。简单的对话又结束了,继续上行!



在递烟和接烟的过程中大家慢慢和我聊了起来,我递出的是十几块一盒的烟,接到的是大概两块钱左右没见过牌子的烟,而且多数时候舍不得点燃。你是从哪里来的呦?为啥子要拍我们?你带来的照相机好多钱......这样的对话越来越多,我知道了他们中大部分人是来自四川阆中,很多同乡。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,但他们却很小心的回答着。四个多小时的走走停停,终于到了山顶的贺兰石矿,说是山顶,却并不是周围最高的山。
苟宗德在看矿人的房子边拿出了一个笔记本,上面歪歪扭扭的写着日期和很多名字,参加背水的背夫也聚拢过来,鄢军四块、熊正文四块、曹金发四块......苟宗德在笔记本上写着难以辨认的名字,他告诉我,这样背水上山每桶睡水老板给四块钱,如果每天都背水山上,一个月就能多挣一百块,不少钱啊!说完,又靠在土墙边去记名字了。四块钱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只是一瓶饮料,一小时的停车费或是一包品牌纸巾;而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?

又是鄢军和苟宗德,后来才知道到山顶的矿上还有活要干,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这样的工作机会,只有老板觉得合适的人才可以挣到这份一小十块的工钱。打炮眼、清渣,当其他人已经开始捆绑将要背下山的贺兰石块时,他们俩在为这几十块钱努力着。



将近中午一点时,大家都停下了手里的活,鄢军从一个使用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塑料袋里拿出两个馒头递给我:你没带吃的,中午把这两个馒头吃了吧!我说不用,喝碗粥就行。他又说,喝粥吃不饱,快吃快吃,我还抽你那么多烟呢!说完一脸不好意思的憨笑。饭前便后要洗手,大家还是保持着很好的卫生习惯,但那双结实粗糙深陷泥土的双手洗后却和之前没多大区别。



吃了一个馒头,留给鄢军一个。大家稍作休息的时候我仔细看了看他们用来背贺兰石块的背架——几根木条被长钉固定成“A”字形,两条背带是用尼龙绳外包纤维袋装订而成,在下山的路上我看到了这样的工具对身体的伤害。


下山,每个人身背一百公斤左右的石头,走路的姿态马上老了20岁,并且不能像上山时大家聊着天走在一起。每隔30米就会有一处歇脚的石台,休息时背夫会吆喝一两声“嘿——哈——”熊正文说,背石头下山,全身肌肉都很紧张,停下来喊一声很舒服,这样也算是告诉不远外的同伴我开始向前走,你可以到这里来休息。
意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,我摔了个很瓷实的跟头。人没什么事,镜头磕在石头上,变焦环变形不能转动!坐在那,看这自己的户外登山鞋,再看看站在旁边伸手拉我的鄢军脚下的黄胶鞋自嘲了一下,平时话语不多的鄢军用四川普通话突然问我,你这鞋好多钱?熟悉之后他也会开玩笑。
再次休息的时候,他脱下了厚实的劳动布上衣,露出了背架和背带摩擦身体的痕迹,腰部和肩膀的新伤压旧伤,这样的伤口基本长不好。他从1997年就开始在这里背石头,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年轻力壮的背夫?他告诉我,现在的年轻人吃不了这个苦,以前来过年轻人,但没多久都走了,他要趁着身体好的时候多背些,把女儿后两年的大学学费挣出来!




这就是那个让我难以忘记的背影,负重着超过自己体重的山石,那些重量是疲劳、是责任、是希望、是无奈、或是对家人的思念。

往返18公里山路,距离住地越来越近,坡度变缓,大家的脚步更快。从背架上卸下石块前我曾试着背了一次,站立没问题,但基本无法行走,重心在背后不定向的摆动。在老板每天一次称量石块的时候,大家都盯着那块称上的小小配重,那是一公斤一块四毛钱的心血,那是鄢军女儿的大学学费,那是苟宗德对家乡田地和老婆的思念,那是曹金发儿子结婚的聘礼,那是孝敬父母的衣裳......

每过一段时间,会有收石头的商人会上山带走这些贺兰石,这个宁夏境内唯一一个合法开采贺兰石的矿,从清朝便开始开采。

在住地土平房里我看到一头驴,无所事事的望着背夫。我问背夫们,有驴,为什么还要人背?背负们大笑,它不行,背不了,就是个宠物。他们告诉我,以前试过用驴驮石头,但摔死过,所以这个活只能人来做!

洗澡、换衣服、吃饭,然后就没有然后了,住地没有电,只有一个小型的风力发电供做饭时使用,他们的手机只有需要打电话时才会开机,没有广播,没有电视,房间里只有一张四角用砖头搭起来的木板床。共十天分两次的拍摄,和他们每天一起爬山,让这些背夫们把我当成了朋友,在我拍摄时也更无视我,更会在我拍片时去玩扒裤子小孩的玩笑开心一下。在我第一次拍摄完成后,鄢军问我还会不会再上来,我说会的,我会再上来一次。他说可不可以帮他们带些电池和常用药。在第二次上去时,我给他们带去了电池、药、西瓜,还有他们每个人的照片,大家都互相比谁更难看。最后一天,我没有和他们一起上山,因为累了,也因为有些难过。






最后一张图,这便是宁夏五宝之一的贺兰石雕刻为砚台的样子,从一块坚硬锋利的原石变为文房四宝中的一员,谁能想到这其中的过程。石头如此,也许人也如此。

时隔整四年,他们还好吗?
我不擅长对文字上色渲染,也不会讲太生动的故事,只是凭着记忆写下这些。只有那个背影和一句话让我难忘,聊天中鄢军告诉我,他的女儿在成都上大学,我问他女儿知不知道学费是这样挣到的并要她女儿的联系方式,鄢军笑着说什么都肯给我“你不能告诉她!她不知道我背石头,她要知道了影响学习就不好了!”